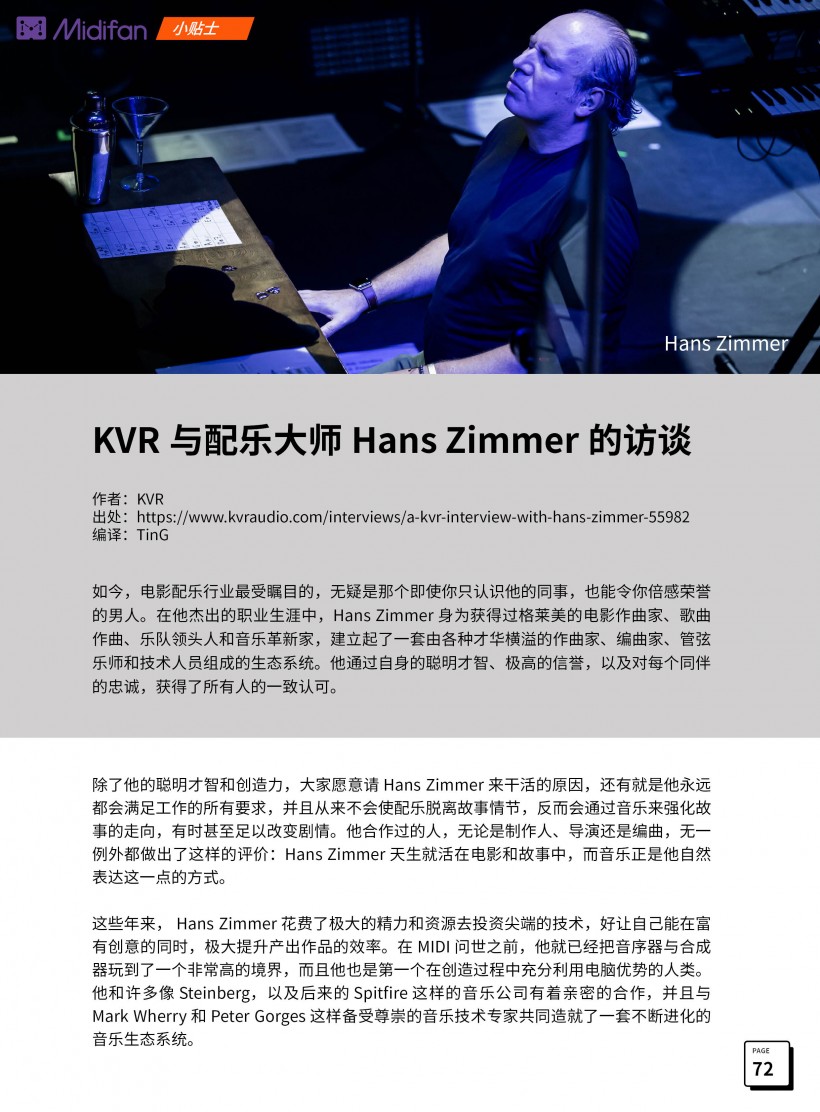与配乐大师 Hans Zimmer 的访谈
如今,电影配乐行业最受瞩目的,无疑是那个即使你只认识他的同事,也能令你倍感荣誉的男人。在他杰出的职业生涯中,Hans Zimmer身为获得过格莱美的电影作曲家、歌曲作曲、乐队领头人和音乐革新家,建立起了一套由各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编曲家、管弦乐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生态系统。他通过自身的聪明才智、极高的信誉,以及对每个同伴的忠诚,获得了所有人的一致认可。
除了他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大家愿意请Hans Zimmer来干活的原因,还有就是他永远都会满足工作的所有要求,并且从来不会使配乐脱离故事情节,反而会通过音乐来强化故事的走向,有时甚至足以改变剧情。他合作过的人,无论是制作人、导演还是编曲,无一例外都做出了这样的评价:Hans Zimmer天生就活在电影和故事中,而音乐正是他自然表达这一点的方式。
这些年来, Hans Zimmer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资源去投资尖端的技术,好让自己能在富有创意的同时,极大提升产出作品的效率。在MIDI问世之前,他就已经把音序器与合成器玩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境界,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在创造过程中充分利用电脑优势的人类。他和许多像Steinberg,以及后来的Spitfire这样的音乐公司有着亲密的合作,并且与Mark Wherry和Peter Gorges这样备受尊崇的音乐技术专家共同造就了一套不断进化的音乐生态系统。
这套生态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管弦音源库。无论何时,Hans Zimmer都非常喜欢与管弦音乐人合作,但这却不太容易实现,因为他经常会工作到深夜。在采样回放设备面世之初,例如CMI Fairlight的时候,他就开始采样各种乐器进行使用了,直到电脑无比发达的今天,他依然在这样做。他在制造采样音源的这一路上,是先从1990年代的Roland S-770和S-760开始起步的,但当时这两台设备的特性,还只能让他在每个设备上使用一个乐器。随着电脑存储周期与内存的不断增加,Hans Zimmer将他的Roland音源库转移到了GigaSampler。大约在2006年,他开始了巨量采样音源的录制工作,并且直到今天,他依然还在这样做,并且这些采样音源也一直在被其团队所使用着。
Hans Zimmer首次对于音源管理软件的尝试是Wizoo。正如所有事物发展的规律,后来Wizoo被Avid看中收购了,而Avid则有自己的开发方向。也还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后来Avid在一轮裁员之中,作为老大的Peter决定离开了Avid。再后来,Peter及其DSP架构师重新与作为个人的Hans Zimmer进行联合,现位于一家叫做UJAM的公司。他们目前正忙着开发下一代的产品,同时协助Hans Zimmer开发他的生态软件基础设施,以支撑Hans Zimmer在伦敦和洛杉矶的工作室,以及与世界各地数十号同为Hans Zimmer音乐事业构想而努力的员工们共同奋战。
Hans Zimmer非常随和,今天我们将与身处伦敦工作室的Hans Zimmer进行一次访谈。
我们都是您的粉丝,这次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和我们对话,我们感到非常荣耀。
作为我的粉丝,我才应该感到荣耀!不过,你们选我当偶像还是挺有品味的(笑)。
您在伦敦和洛杉矶都有工作室。那么这两间工作室的设置是完全一样的吗?
有一些地方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伦敦这边也有一些洛杉矶工作室没有的东西(指Analog Solutions的Colossus合成器)。在我后面是一套Moog的模块合成器,这个和洛杉矶工作室里的是一样的,当然,那间放有我自己定制过的采样器的机房也是完全和洛杉矶工作室一样的。我们是Waldorf Iridium合成器的铁粉,不管在哪都会摆上几台。
Colossus非常是非常棒的合成器。然后我想问下您关于音乐方面和您所使用的技术相关的问题。
好的,反正都是一回事儿。
您的职业生涯已经非常成功了。那么现在您每天起床的动力是什么呢?
说实话,我早上没有任何起床的动力。最迟在晚上12点之前我什么都不会做(笑),但其实我更多的是在下午2点左右开始工作的。不得不说,我已经成功同化了那些在好莱坞的同事,因为对于那些一大清早就给我打电话还不留名的人,我非常擅长假装自己已经完全睡醒,并能与他们展开完美的、合理的对话。然后过了几周,这些人再打电话问我“上次说的工程怎么样了?”的时候,我就会说:“你说的什么工程?”我是这么觉得的,当人们在收到我的第一封邮件而感到震惊之后,意识到了当前的危机有多么严重,这时世界才会开始变得更好。
但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激励着我?这种东西就是想法。还有那些和我一起工作、一起演奏音乐的人。科技也激励着我。在不同的日子里,各种不同的事物都激励着我。你可以说,是未解之谜激励着我。问题激励着我,而答案是无聊的。
您最近的两部作品是《沙丘》和《壮志凌云:独行侠》,里面有一些体现了原著主题或主旨的东西。那么您实现这一点的方法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并没有,但里面有很多东西。这样,我给你说说为什么要接下《壮志凌云》的工作吧。Tony Scott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非常喜欢他。而Jerry Bruckheimer和我合作过很多次,而且我记得Tom Cruise应该一共和我合作过7部电影之类的。然后Harold Faltermeyer和我是邻居。有一段时间,我和Harold、Giorgio Moroder全部住在慕尼黑的同一幢房子里,但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们。我还记得,曾几何时Jerry Bruckheimer只从那幢房子里雇佣编曲,不过我认为这完全是巧合,就是这样。
所以,我为什么接下这个活呢?是因为Tony。因为我喜欢Harold,我喜欢他想要呈现的主题。而且我接下这份活也是因为Tom。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有好有坏。比如,好事之一就是Lady Gaga加入了团队。而且我的朋友Dave Fleming,她也是特别棒的音乐人和作曲家,以前我在洛杉矶时会和她整晚演奏音乐,当时她写了一首情歌,我就觉得可以将其发展成为某种关于“爱”的主题。所以我一直认为,不管在整个配乐过程中,写出了怎样的歌曲,只要能抓住主题就是好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毕竟现在和1980年代不一样了,你不能随便写首歌放进去,然后就不考虑和电影中其余部分的关系了。在《狮子王》中,我就不承认Elton(John)的配乐,他做他的我做我的。不过如今,我会试着以恰当的、合理的方式去加入一首歌曲。与他人的合作为先,然后你还需要让合作的艺人成为团队的一员。这就是我说的好事。
然后坏事就是新冠疫情。我感染了病毒,病得趴在地上都起不来了。不过这时我的朋友Lorne Balfe出现了,他非常有才,而且正好和剧组的各位都认识。他和Tom一起做过《碟中谍》,还和Jerry Bruckheimer做过很多电影。Lorne补上了我的空缺,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我非常喜欢大学乐队那种氛围的工作环境。我也喜欢大家各抒己见,尤其是当我卧病在床,需要他们来帮助我的时候。
但《沙丘》就很不一样了...
《沙丘》完全不同,而且在当时的节骨眼上,新冠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当时我正在经历最难熬的阶段,意识到自己不能再以平时的方法进行工作,所以我把客厅改造成了工作室,唯一允许进入这片空间的只有我的助手Alejandro,他现在也在工作室里当我的助手。所以,如果我开始满嘴跑火车了,他就可以给你提醒(笑)。
好的。我记一下哈...
在当前这种奇怪现状的一年前,我们就开始《沙丘》的配乐工作了。Denis Villeneuve(导演)和我早就决定了要使用女声来配乐。于是我们就找到了世界上最棒的人声提供者Edie Lehmann Boddicker,其实也正是因为他丈夫Michael,我们才发现的Loire Cotler。那么,他是怎么发现的呢?当然是油管了。这年头,除了油管你还能在其它地方找人吗?
所以,我们找到了Loire,她还带着Edie和Susan Waters。Denis过来视察进度时正好看到我们四个人。当时他那叫一个目瞪口呆,因为我们在做的东西是非常有趣的新方向。我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做了一个建筑平面图。然后新冠疫情就又来了。当时我正在家里和自己的旅演乐队工作,然后Loire也加入了进来。这些人基本都是和我一起演奏过很久的,而且他们也都可以在家里录音。
《沙丘》的配乐非常电子化。但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并意识不到它有多电子。我们会使用Zebra的四个共振器,来把藏族号的声音完全转变成Tina Guo的大提琴声。这种玩法会让像Urs Heckmann(u-he的老总)这样的人发疯,我认为Urs会觉得我们是疯掉了,不过最后的结果听起来还不错就是了。
确实不错。如今,比起硬件合成器,您使用软件合成器的频率如何?您有最喜欢的吗?
软件合成器其实很简单。是这样的,我确实喜欢自己手里的硬件合成器,但我觉得在疫情期间,不适合把工作室墙上堆放的合成器扣出来用,毕竟我人还在不同的地方。这正好也有助于我们的木管乐大师Pedro Eustache发挥自己的作用,因为他在暗中其实还是一个合成乐器演奏者。他有两台原版的Lyricons电吹管。而我,则非常了解Zebra软件合成器,也就是ZebraHZ版本,或者黑色的Dark Zebra,这是我的专属版本。我喜欢制造不同的声音,于是留给我音乐编辑的工作就不多了,所以他经常会说:“好吧,又到了让我写音符的时候了”(笑)。
所以,我最喜欢的软件合成器就是Zebra,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它潜在的音色质量从来不会让我失望。每个模块的代码写得也非常棒。它的振荡器很好,电路设计也很好,里面只有一个模块有点不好用,但是其余的地方质量都很高。
而且我喜欢它那种专为软件设计的GUI,而不是一味像硬件模仿靠拢。许多年前,在Arturia发布他们的Modular Moog软合成器时,我就体验过这一点。所以,我最终花费了和操作身旁的硬件一样长的时间,却做出了不一样满意的音色。有一次,我和Urs说:“模拟世界有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数字世界又太过完美了。”然后Urs就咆哮回复到:“你懂个屁!模拟才是完美的,数字反而不完美。模拟世界完美就完美在一切都是直来直去,里面没有计算,也就没有计算可能带来的错误。正是天才的设计加上天才的部件搭配,才让它这么完美无暇。”
而我喜欢Zebra的第二点,是它总能给我带来惊喜。因为我总是喜欢先随便玩玩,想着每天是不是都要用不一样的合成器试试,结果玩着玩着,Zebra就能玩出不一样的。所以它永远不会让我感到无聊。直到今天我都还能用Zebra玩出新东西。所以,你前面的问题,我每天起床的动力是什么,合成器也是其中一点。那我选择合成器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声音听起来让我喜欢,然后不让我觉得无聊就行。
您在配乐时,是否经历过自己的音乐改变了故事情节的情况?
当然有。我可以举几个例子给你,但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是《角斗士》,那部片子直接是在我的工作室剪的。
电影剪辑吗?
没错,他们在我工作室做的电影剪辑,因为这样才有意义。我在Barry Levinson的剪辑室里做了《雨人》的配乐,在Gore Verbinski的剪辑室里做了《女海盗》2和3的配乐。所以,只有我们都聚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
电影一般都是先从讲故事开始的,之后才会进行到战争等场景,而《角斗士》正好缺少故事情节。于是我一直在说:“Ridley(导演),你可是诗人和艺术家,但你却并没有给自己相应的自由。你并没有向观众呈现出来你是个诗人这一事实,而且里面也没有体现出女性的灵魂。真的。”
所以,我们就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剪辑师Pietro Scalia的架子上放了三张CD,其中有一张是Dead Can Dance组合的。当Ridley认同了在电影中加入女声可能会是很有趣的想法之后,就拿出了那张Dead Can Dance乐队的CD,然后说:“请Lisa Gerrard来唱怎么样?”而现场正好有人有她电话。其实我从来没见过Lisa,但Ridley和我说这样正好。于是第二天早晨我们回来时,Pietro就翻出了那个手在小麦上放了一分钟的镜头,电影的开场就这么敲定了。试想一下,如果你的电影一上来就是长达一分钟的把手放在小麦上的场景,没有对话,只有音乐,甚至连个标题都不给,那么这个场景很可能就是第一个被从剧本中删掉的东西。
我还记得在洛杉矶时,Nolan正好在伦敦做他的第一部《蝙蝠侠》电影,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在拍摄蝙蝠侠站在摩天大楼上俯视哥谭市的镜头时遇到了一点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拍好这个场景。这个镜头本身很棒,但我们必须把它拍出标志性的感觉。”他向我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我就为他提供了一些能让这个镜头顺利进行的大概想法。
就像《对话尼克松》一样,我记得当时和Ron(Howard)什么都不做,专门整整讨论了两周音乐、歌曲和构思方面的东西。于是乎后来每天的胶片中就出现了一些镜头,我一看就知道是受到了音乐启发的、有助于电影情节发展的那种,而且都是我向他“画饼”说拍出来我肯定能配的那种,而不是先配乐再拍。
MIDI(乐器数字接口)现在差不多已经有40岁了。MIDI对您的职业生涯有过什么改变和贡献吗?
MIDI拯救了我。我以前用过Roland Microcomposer,当时还需要输入数字,然后通过控制电压来进行使用。当我可以用8轨音序器写歌的时候,真的非常开心。从一开始我就觉得,MIDI是非常棒的东西。我知道MIDI有延迟,不过我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也知道MIDI当时不是很稳定,但我也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不过MIDI可以做得事情远比操作使用门信号的控制器要多,到那时为止我一直是这么用的。
不过我后来停用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想起了早期过渡到MIDI时的情景。我有一台Fairlight采样器,它诞生于MIDI出现之前。没过多久,厂家就在后面安了一个MIDI接口。后来事实证明这样做非常明智。但Synclavier就不是了,他们非常傲慢,不想在设备上安装MIDI接口,因为他们觉得MIDI是一种不合格的协议,可不是么?就凭那些小小的针脚?但是,你刚才说了句什么来着?MIDI已经有40年历史了?
MIDI诞生于1983年
是的,和我的职业生涯长度有的一比了,所以这应该足够回答你的部分问题了。但还有一方面,MIDI是目前所有电脑协议中最稳定的一个了。我有一些朋友,原先都参与过苹果系统的编写工作,不过现在已经不太出名了。我不知道现在的Mac OS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但我的朋友们每次更新过后,都会忍不住说:“我去,我小时候写的代码怎么还在里面!那些东西写得也并不是很好,但因为是缺了就没法运行,所以才依然保留在里面吧?”协议长时间不变的情况是非常少的。我还记得Jeff Rona和Chris Meyer,他们非常有才,曾在制作MIDI时间码时为Roland工作过。二人曾为这项工作投入过极其伟大的创造,而且因为当时是限制在8Bit系统上,大家都在想办法充分利用系统的每一寸资源。
我能想起的和自己的工程师Steve Lipson的点滴,只有关于以上话题的讨论,他通过MIDI制作过非常伟大的唱片,比如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的许多作品。当时,他还说到了1980年代在音乐行业蔓延的某种“塑料”质感,并认为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我认为这与MIDI协议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有这种协议的存在,所以突然间谁都可以编写VST合成器和效果器了。
而且,我们必须对Steinberg发明MIDI协议这一行动给予高度的赞扬。我记得有一天,Propellerhead的人来到我的工作室,给我了两款模仿自Roland 808s和303的软件,他们说:“嘿,这是我们最新出炉的产品。你觉得这两款虚拟乐器如何?”当然,我认为两款软件都非常棒;当然,我也有原版硬件。之前我说过我们这有很多台Waldorf Iridiums,而且并不是装在电脑里的VST插件,如果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的话。这些才是带触后键盘的、正儿八经的合成器,所以和VST是不同的。但VST插件也很棒,它们的生命力依然旺盛,现在距离1980年代已经过去了许久,而且据初代VST也过去了很久...只不过VST可以看起来像一台Mini Moog,但听起来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鉴于您始终走在音乐世界的最前沿...
哎我没有我没有,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你还是小孩的时候,千万不要当你们那片邻居里第一个拥有微处理器或软件的娃,否则夜里一旦崩溃,你就赶不上Deadline了,非常麻烦。曾经在伦敦有个制作人叫做Steve Levine,所有Culture Club的唱片都是他制作的,我的工作室就在他的旁边,所以每当他接触什么新玩意儿时,我就可以在跟风购买之前先观察一下。如果我发现隔壁的地板上出现了薅掉的头发,或者穿白大褂的人(急救人员...)出现的话,那我就知道这些玩意儿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才能成熟。
其实这也正是我想问的。您曾经遇到过Deadline逼近,但是某个部分出了问题,导致无法正常完工的情况吗?有的话您又是怎样处理的?
有过,当时我用的是第一版的Pro Tools。我们用Pro Tools完成了全部的电影内容,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有一个场景一共有256个剪辑,但我们的工作完成地非常完美。然后等我们拿着东西去找Lucas Ranch的时候,就播放不了了。然后加州Palo Alto的工作人员全部赶了过来,想尽办法也无法恢复正常,所以场面一度非常尴尬。于是可怜的音乐编辑不得不重新把这些剪辑又做了一遍。所以,那时真的非常麻烦。
听着就难过。我们再说说采样吧。您在这些年里制作了很多音源库,而且我也知道现在您正在和UJAM合作,可以说说吗?
我上周刚见过Peter Gorges。很多年前我们开始制作一款软件采样器,因为当时的Kontakt还不能满足我的需求。针对电影行业的工作 ,全部都需要在环绕声中进行,但Kontakt并没有相关的功能。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非常定制化的,就想让它专门做好一件事情。我们想做一套参数固定的管弦音色,然后里面有木管乐器、弦乐器、管乐器等等,但Fuzz和失真效果就不需要加太多进去。
所以,我们就着手开始制作这样一款可以播放管弦音色的软件。而在开始之后的不久,Digidesign就跑过来说:“你们的软件太棒了!能卖给我们吗?”当时我并不打算阻止Peter出售这款软件,所以我的第一台采样器就通过Avid/Digidesign面世了。然后,我那优秀的旅行家朋友Mark Wherry对我说:“现在你的采样器到处都有人在用了,但你自己想要的采样器却没有了。不过,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所以,他又为我们制作了一款采样器,那款采样器即使放到今天来看,在其工作原理上也是十分具有革命性的。
接着,随着行业的起落沉浮(如果你入行足够久的话,就会看到这种现象),Digidesign的元老不断被开除,这就意味着我的初始团队,包括Peter等人突然又可以和我一起工作了。到当时为止,我们的采样器就已经非常优秀了,而且还带有一个编辑器,而开发了这款采样器的人后来也为Steinberg开发了HALion。在那些天里,我们的采样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支持了多轨道的功能,而且还是无损采样。所以我们转而开始在各种空间里详尽地、非常有针对性地采样各种不同的管弦音色。
而有趣的是,我们采样过的一些声音会遇到各种情况。比如我喜欢的演奏家会退役;大提琴手也会抵挡不住诱惑而将Stradivarius大提琴卖给香港的收藏家,这样世界上就又“少”了一把原版的琴。除非他在出售之前,我就把他找来,强迫他连续两周坐在我的录音棚里,把我们能想到的所有音乐方面的可能性都录制下来,所以我们的有些东西甚至是具有考古性质的。就像是,为了让事物存活下来而采取的行动一样。
所以,您收藏的不仅仅是乐器,还有演奏者...
没错。曾经我遇到过一位技艺娴熟的双簧管演奏家,但双簧管演奏这种事情是有明显年龄限制的。因为随着年龄增加,你的嘴唇会逐渐失去力量。他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担心自己无法再演奏出优美的声音,所以跑到了泰晤士河的桥上,把他的双簧管给扔了。如果我不在他的巅峰时期就把他的声音采样下来,那这就是这份声音的最终下场。所以,我们的采样工作真的非常细致,每一处细节、每一处动态,所有的东西都会详尽考虑到。
所以也包括环绕声的细节...
我们的采样器,和其它采样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里面有额外的音色层,使用了32支麦克风来录制任何你想要的环绕声结构。所以,我们并不考虑现在那种常见的环绕声制作方法,也即通过环绕声麦克风录制,然后依然使用混音来组合音色的形式。我们可以随时回溯到原始录制的麦克风。如果想要声场比较近的声音,我们也可以随时移除氛围声;当然,我们也可以随意对音色做出很大的调整。
所以,您的音源是完全基于演奏者、乐器和配乐目的而建立的吗?
就是基于所有这些东西建立的。但有一点比较重要,那就是我必须要用演奏者坐在大厅的规定的位置上,面前放支麦克风,让他按照配乐的风格来演奏的东西。很多时候,演奏者听到我的Demo之后,都会直接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用呢?”我就会回答说:“不不不...我给你听这个,是因为你必须现在录一遍。你并不用做到完全地一模一样,但我想要的是人类的感情在里面。我想要的是那股激情,我想要的是人类能做到的各种细节。”不过,因为我所追求的是真人演奏,所以真人演奏有时候会出错,比如弹错音符什么的,这时我就可以替换1小节或者多小节的采样。反正也没人能说出来哪里不同。
您的意思是,可以把录音的某部分用一些采样替换,然后修正错误的音符部分?
替换的还是同一个人坐在同一个大厅里、用同一支麦克风录出来的东西。或许重录的会有一点点不同,但只是一两处的话就无所谓了...你看,我做过很多百分百纯电子的配乐,但是大家都认为是声学乐器做的,反过来也一样。
那我还有哪些应该问您但还没问到的问题吗?
没了,真要问起来1000个问题都不止,但总之今天是没有了。其实一切都很简单,我认为,目前我们仍然处于科技的最开端。不像钢琴,它至今已经有了600还是700年的历史了。我们正站在科技的开端,这非常有趣。此时,你唯一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声音的潜在质量是否优秀。就这样。重点在于,科技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音乐制作了...你并不非得成为千万富翁,才能买得起做音乐的好电脑。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我是个“老古董”了,所以我就以你们的视角来说,我敢打赌未来你们一定可以通过iPad来进行配乐的工作,绝对没问题。
或许您也可以。
实际上,真正的秘诀就在于,不管你用什么工具,都得产出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一切。
可下载 Midifan for iOS 应用在手机或平板上阅读(直接在App Store里搜索Midifan即可找到,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直接下载),在 iPad 或 iPhone 上下载并阅读。